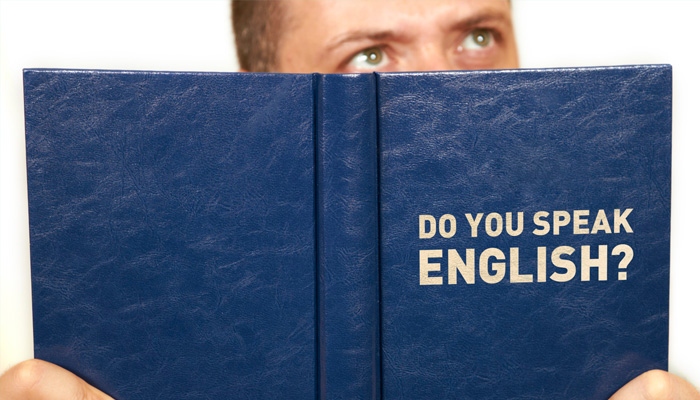在亚洲援助部门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援助工作者把他们工作重心放在了在英语教育。来自澳大利亚政府义工计划的负责人建议我们不要把NGO工作变成“制作人类的字典”。而在中国我所在的那个地区,美国和平队的其中一个战略是派遣志愿者“只”教英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太批判性的策略,“多么像语言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当地的NGO同事和一些所谓的“政府发展部门”的行政人员经常要求我们这些能够讲地道英语的人:跟他们讲英语,校对和起草英文报告,申请助学金,翻译该组织的网站,帮助留学生申请海外大学和给他们朋友的孩子做英语家教。这些事情也经常引发一些志愿者抱怨,例如“我觉得我来这里主要就是做翻译工作”和'我每天都是做校对和管理的任务,我看不出这能有什么建设性作用”。
当你漂洋过海来到国外,却发现除了“你有一张白人面孔”或者“你是一个外国人”之外,当地人并不期待你能做些别的事情,这多么令人沮丧。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只有白人才讲英语,虽然这是许多母语是英语的国家确实白人居多)。但是英语的援助作用到底是不是被低估了?
事实上“英语工作”并不会做不好,因为援助工作者总有一些优越感。这些援助工作者都在某些领域受过专业训练,例如环境科学等领域或公共健康,并相信他们是被雇用来在这些领域做出贡献的。另外,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认识到,他们并没有专业的语言教学经验。大多数援助工作者是严格的全球公民,对于语言帝国主义也会非常的警惕。但我认为,这些所谓“很好的理由”并不恰当。
错误的技巧
如果没有受过教学技能的训练,那么无疑的你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教学候选人。但是在我讨论到的这些地域,学生要找到这些受过培训的英语老师或者母语是英语的非师范人员都是很不容易的。虽然美国和平队可以接收到一些受过教学训练的志愿者老师 并派去那些紧缺英语教学人员的贫困地区教学。更重要的是,对于所有人的第二语言获得(SLA),很重要的学习时机是在课后以及成年之后:例如说课后与援助工作者的交谈或者与他们成年后伙伴的交谈,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曾经向人们展示了与相互了解的同伴交流,这种伙伴团队学习模式对语言的获得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这里面并不需要老师的帮助。在这种学习模式下,不管是语法的结构还是在不同语境中的恰当表达方式都能被学习者有效吸收。总之,不管是协助同事完成英语任务,还是说只是日常谈话,都是语言学习者宝贵的学习机会,这是每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帝国主义倾向
在许多国家,人们普遍觉得会讲地道英语的人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既然当地居民觉得说英语是非常上进的事情,那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呢?相对于那些许多青少年和成人想参加却无法参加的特殊援助项目,特别是那种只能为部分儿童提供,昂贵的、名额稀少的正式语言课程来说,机构同事和居民发现这些说英语的志愿者带来的非正式的课堂外的英语练习更加有用。
就像Kamwangamalu在笔记里面描写非洲的情况一样(我发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利益相关者拒绝使用自己的方言[...],因为他们认为方言毫无用处,在语言学市场上没有价值”(2013 Kamwangamalu)。在这方面,当地的利益相关者是没有错的,英语在许多市场确实有着巨大价值。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会说这是语言霸权的证据,而且那些母语并非英语的人宁愿自己的语言被英语统治,这就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同谋。即便如此,难道说在这些讲英语的志愿者入驻的地方,反对霸权主义就是拒绝去教人们英语吗?
通常情况下,英语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上的能力和资源,对国际援助行动来说尤其如此。当地的所谓精英阶层总会用英语来显示自己地位,这让非精英阶层的人觉得英语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例如,加纳人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用方言作教学媒介是一个微妙的精英策略,这样可以保持下层人士继续被边缘化,而主流人士继续精英化。”
不管我们是不是反对所谓的英语在意识形态上统治,使用英语毕竟有利于校对合作人的捐赠报告,制作有效的办公模板以及在活动方便组织者与受助人的交流。越多的合作者愿意出席这些活动就越好。那些志愿者经常遇到的请求——帮助朋友的朋友完成他个人的英语任务,同样应该接受,因为语言能力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充当集体资源。事实上,现在许多语言学家主张研究“实用语言学、交际、符号资源”,而不是单纯的“语言”(Blommaert,2010年,第102页)。英语资源可以让整个社交网收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在用英语扩大社交网的过程,也是在减少不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影响。
国家政治和国际发展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英语在这些领域中有经济价值也有象征意义。 对于能够说地道英语的人——特别是专业援助志愿者——可以用较低成本完成专业英语的注册工作。因此,他们可以非常高效地完成需要用到专业英语的任务。重要的是,这不是一种以长远效益为代价的短期效率:协助机构同事完成英语任务不会阻碍他们获得英语能力。相反,它还扮演了一个“改善现状”的角色,培养机构人员学习专业英语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少。讲英语的援助工作者做这些“英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客户的物质支持,以及他们的能力可以在国际平台上展现出来。
这些流动性的志愿者、组织以及整个公益社会网络付出的效益确实很难抵消所谓的语言帝国主义对社会的损害,但不应该把责任推到“英语援助工作”上。
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语言的流动》(Language on the Move)上
References
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Kamwangamalu, N. M. (2013). “Effects of policy on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Africa.” World Englishes 32(3): 325-337.
Mfum-Mensah, O. (2005). “The impact of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hanian language policies on vernacular use in two northern Ghanaian communit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41(1): 71-85.
- See more at: http://www.whydev.org/we-do-aid-not-english/#sthash.yW9LZ5Tj.dpuf
----欢迎转载,但请保留本段文字——“本文来自有趣又有用的公益资讯资讯平台创思客(thinker360.com),译者/作者 苦瓜脸”---